阅读:0
听报道
01
今天说说《少年的你》。
我周末看了这个电影,心态有点复杂。要说这个电影不好吧,其实拍的还是挺好的,阴暗的气氛渲染得不错,演员演得也到位。要说好吧,但它总给我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它让我联想到了《白夜行》。
但是跟《白夜行》比起来,它要柔软了好几个等级。《白夜行》就像一把冷冰冰的刀,看完以后有一种堵在胸口的感觉。《少年的你》则要温柔得多。开始它可能擦伤了你,但擦伤完了它会给你包扎好,拍拍你的肩膀,把你送出电影院。
大家还记得《权力的游戏》吧?最后一季里编剧大发神威,寥寥几笔,就把一匹骏马改成了骡子。《少年的你》也多少有点这种感觉。当然,这也许不能怪导演和编剧。他们要是拍出一个《白夜行》那样的东西,恐怕很难上映。
这么改动之后,《少年的你》主要就是一部“社会问题电影”。既然这样,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社会问题。
02
说到校园暴力,就得谈到孩子。
人会悲悯,会仁慈,是因为人有共情的能力。别人受到痛苦,我们能想象这种痛苦,感受这种痛苦,所以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让别人受苦。
共情能力就跟其他能力一样,也需要慢慢养成。总的来说,孩子的共情能力比成人要弱。
所以大部分成年人做坏事都有具体目的。
我让你痛苦,是因为我能从中得到好处。你要是疼,那没办法,你就忍着点吧。
但是孩子不一样。他们让别人痛苦,往往就是单纯觉得好玩。我有能力让你痛苦,这件事很酷。仅此而已。你疼不疼的,我完全无感。
而有一些孩子天生就容易变恶。
我们说:孩子都是一样的。
其实并非如此。任何一个父母,都能体会到:每个孩子来到世上,都带着自己先天的个性。
有的孩子很快就发育出强大的共情能力,心地善良。但有的孩子天生就没有这种能力,而且也永远不会有这种能力。
他们身上有恶的种子。
《少年的你》里那个魏莱,明显就属于这种孩子。电影里头,她坏的很突兀,几乎毫无道理。这个倒不是导演的疏漏。因为有的孩子就是这样,坏得毫无道理,坏得难以理喻。
03
既然有恶的种子,那长大以后他们百分百就是坏蛋吗?
那倒不是。
有本书叫《天生变态狂》,是一个心理学家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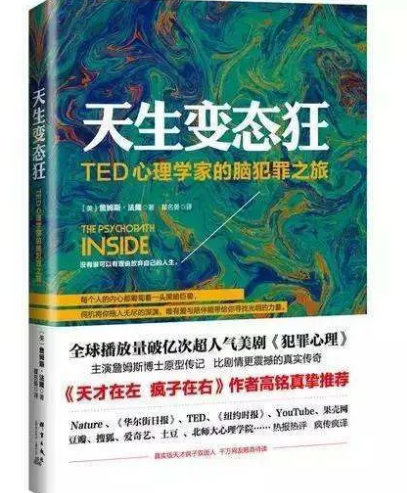
这位心理学家有一阵子研究变态心理,看了很多变态狂的脑部扫描图。看着看着,他发现一件事:咦?我的脑部结构怎么跟这些变态狂的这么像?变态狂这一块区域发达,我这一块也发达;变态狂那一块区域萎缩,我那一块也萎缩。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又查了查自己的家谱,又有一个惊喜:
祖上盛产变态狂。
他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自己其实是一个天生的变态狂。
那他为什么没有当街裸奔,杀人放火,猥亵小朋友或者肢解动物,反而当了一个心理学家?
这是因为他成长环境比较好,压制了自己的变态倾向。而且多少有点偶然,他发现了自己其他方面的才能,靠这种才能找到了存在感。
所以,他没有变成一个反社会的坏蛋。
但是他跟正常人就没有不同么?环境有没有他改造成一个善良体贴的暖男呢?
并没有。
这位心理学家对自己的变态还不太放心,就问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你们觉得我这人咋样啊?
一半左右的人笑笑不说话。另一半的人回答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跟你在一起很开心。但是总的来说,你是个烂人。
一个密友告诉他:
我真的很喜欢你,愿意和你相处。但我不能相信你。要是发生什么糟糕的事儿,你根本指望不上。
这位心理学家终于搞明白了一件事:
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反社会,而是成为一个既有用又有趣的。但是,他始终没有同情心。他自私,冷酷,不在乎别人,缺乏共情能力。
他天性凉薄,这一点无法改变。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天性是第一位的。它是人的底色,无法扭转。但是环境也在起作用。有的人天性有邪恶的种子,环境可以触发这种邪恶,也可以选择不触发。
就比方说《少年的你》里面的魏莱。她不可能变成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她有可能长成一个正常的烂人,甚至还可能在人群里显得特立独行,有所成就。
但是她绝不可能变成一个大好人。

而小北呢,即便活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见的都是最残酷的东西,但是他依旧会保有一份善良。因为他的基因里刻着五个字,让他无法摆脱。
这五个字就是:你是个好人。
这种看法是不是准确,我不能确定。但是根据生活的经验,我觉得至少有一定道理。同样的环境,就是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就是天性醇厚,而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也没用。你永远不可能感化他。
04
像魏莱这样的人当然很少。但是这种人往往有一种天然的领导力,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他们会招徕几个喽啰,欺负弱小。这些人就像一群鬣狗,能从一群角马里头,本能地嗅出最合适的受害者。
这样的受害者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缺少朋友。
落单的角马就容易倒霉。
在青少年时代,最能保护孩子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朋友。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少年时代。凡是有两三个好朋友的,极少会成为霸凌对象。
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不好欺负。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少年都有强烈的从众心理。落单的少年是不被接受的。
少年看上去喜欢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实际上,他们一点都不特立独行。相反。他们是天生的群居动物。
少年需要被某个团体认同,渴望跟这个团体里的人保持一致。他们的自我需要投射到某个团体里面。
成年人的孤独是一种寂寞。而少年人的孤独几乎是一种原罪。自我无法承受,外界无法原谅。
人的整个一生中,最需要朋友的阶段,就是少年时期。对于少年来说,朋友是他的光,也是他的盾。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交际状况。孩子有没有朋友,比孩子有没有好的成绩更重要。
在《少年的你》里,陈念最大的软肋,不是她妈妈欠债跑路,而是没有真正和她站在一起的朋友。如果她有朋友,魏莱可能根本就不会动霸凌她的心思。
对少年来说,孤独就像从身体里滴出的鲜血,自然地会招徕鲨鱼。
05
跟成年人比起来,少年的世界更容易弱肉强食。
如果我把你打一顿,那么我会付出代价。至少要赔钱,说不定还要拘留。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打了一顿,会怎么样呢?
很可能不会怎么样。
也许家长会来闹一闹,也会老师会批评一下,也许要赔礼道歉。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而且很可能连这个都没有。
孩子嘛。
网上经常有人说:孩子被欺负了,家长应该怎么做?
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告诉孩子,打回去!
如果街上有个壮汉把你打了一顿,你去找警察,警察一拍桌子:没用的东西,怎么不打回去?!
你心里头会怎么想?
那你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求孩子做到呢?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扔进一个丛林世界里,让他们咬回去?如果他们有咬回去的能力,又有几个人会被霸凌呢?
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给孩子打造了一个黑暗森林。就像那些恶性的霸凌事件,成人世界里很难出现。不信,你扒光一个大姑娘拍裸照试试?但是在少年世界里,这样的事情有时真的就默默发生了。
那些少年的绝望,真的是难以想象。他们就像生活在一个残酷的动物世界里,就像洞穴里的老鼠一样,战战兢兢,看不到光亮。
06
前两天我读了一篇公号文章。今天我评论《少年的我》,多少就跟这次阅读有关。
这篇文章问了一个问题:
魏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但她犯下的错,值得用生命付出代价么?最重要的是,多年后的陈念应该长大么?
按照作者的意思,影片的结尾应该是这样的。
陈念从路旁轻轻采了一朵野花,默默放在台阶上——为自己,为魏莱,也为所有走过来的残酷青春……然后小北被陈念的举动惊愕,两个人对视,然后露出灿烂的笑容。
作者说,他本人的泪水“会在这个时刻决堤”。
读完这段描写,我几乎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说实话,读于丹都没有这种感觉。
这不是把一匹马画成一头骡子的问题,这是直接拿着刀子上去阉啊。
要求大家拥在一起抱头痛哭,“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可怜的人!”,这虽然满足了大家扮演上帝的欲望,但却是一种赤裸裸的伪善。
魏莱的邪恶当然有她背后的原因。如果我们从魏莱的角度拍部电影,那当然会是另一个版本的凄惨故事。
就像《天生变态狂》里说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可能会抑制她的恶,让她成长为一个凉薄冷漠的普通烂人,但不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她甚至可能会找到幸福。所以,在她背后当然有环境的错。
是啊,哪个邪恶者背后又没有一段悲剧桥段呢?
卡波特就曾站在一个变态者的视角,重现了一段真灭门惨案,那就是著名的小说《冷血》。在这本书里,他用一种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这个杀人犯。
但就算是卡波特,也没幻想过如此肉麻的场景,更没有被这种肉麻的场景感动的泪水决堤。
因为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去理解魏莱,都可以拿朵花致意她的残酷青春。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们唯独不能要求陈念这么做,唯独不能要求她“放下”,要求她把遗忘美化为“成长”。
是的,魏莱死了。可她是在干了什么之后死的?
我们凭什么要求陈念被践踏、被羞辱、被拍裸照,在整个青春都被毁掉之后,还要为魏莱送上一朵野花?
如果换成是我,我绝不会在台阶上放上一朵花。
如果我是小北,那我更不会。
无论是陈念,还是小北,他们不需要旁人决堤而下的廉价眼泪。
07
谅解是一种伟大的东西,需要巨大的力量才能承担。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把这副担子放到别人肩上?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用伪善的泪水骗诱别人来承担呢?
就像《白夜行》里的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期盼着他们在当年那座废弃建筑里,为被杀死的施虐者放上一朵野花呢?
当那两个孩子孤独地面对黑夜时,你们的光明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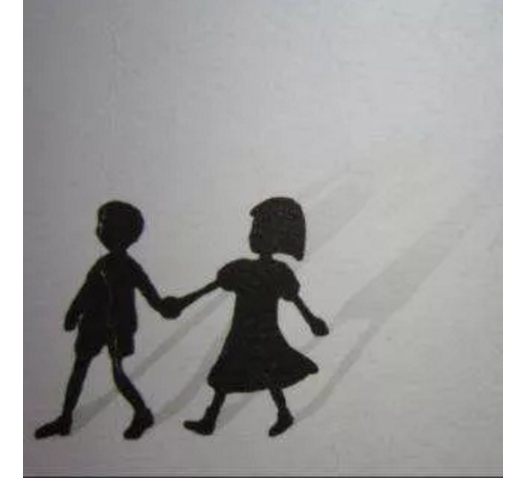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