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谈历史,写到哪儿算哪儿吧。
01
在很多人印象里,儒家非常强调忠君,甚至到了愚忠的地步,什么“君为臣纲“,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都是他们搞出来的。其实,这里多少有点误解。
先秦儒家对君主是比较平视的。孟子就说“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在这里,君臣之家类似于一种相对的契约关系。
但是对父子关系,孟子就不会这么说。瞽叟怎么害舜,舜都要孝顺瞽叟,不能说“父之视子如土芥,则子视父如寇雠”。因为在先秦儒家的道德观里,人伦关系至高无上,是目的性的存在;而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这也不光是孟子一个人的想法,荀子谈起君主来,也多少有点这种味道。
只不过到了秦汉以后,帝国已建,天网已成,儒家知识分子不敢这么高调了,不敢随便说话了,才有董仲舒之流的人说什么“君为臣纲”,把彼此关系绝对化了。
但话是那么说,实际上读书人心里怎么想的呢?
恐怕未必真那么忠心耿耿,就像朱熹在做《四书集注》的时候,注到孟子的那段话,也说“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看不出有什么“愚忠”的地方。
这其实很正常。儒家“人伦高于政治”的核心观念并没变,也没法变。就像魏晋之时,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大家曾经热心地讨论一个问题:“皇上和爹爹都病了,手上就一丸药,谁吃了谁活,那应该把这个药给谁?”。当时的太子曹丕拿这个问题问名士邴原,邴原“勃然曰”:“给爹!”曹丕就不说话了。
在邴原脑子里,提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无耻的。皇帝凭什么跟亲爹比?要是把药给皇帝,不给亲爹,这还是人吗?
在儒家的伦理体系里,只有父母的权威才是绝对的,君臣之间不是,夫妻之间当然更不是(《左传》里说“父则一尔,人尽可夫”,在儒家看来,这话也许有点轻佻,但排序上并无大错):好爹妈是爹妈,坏爹妈也是爹妈。至于君主,他们骨子里采取的是“绩效主义”:干得好你是君主,干不好你是独夫!群众就可以弄你!
后来读书人一方面弄怕杀头,一方面想做官,会说一些类似“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之类的话。而且这种拍马屁的事本来就会卷,越卷越没底线,这种事情也是有的。但是归根结底,这绝非儒家的原意。
当然,“君为臣纲”之类的话说多了,有些死心眼的读书人也会信。但是真正精英文化人恐怕还是不以为然。就拿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他们来说,他们无心出仕,更加放飞自我,敢说一些真实的想法。
王夫之谈到刘裕的时候,就说刘裕能收复汉人的土地,篡位就篡了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谈到桓温时,他也说,要是桓温真北伐成功了,回来篡位也没什么不好。这种想法就跟顾炎武很接近。帝王喜欢把社稷和天下混为一谈,顾炎武就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跟亡天下压根不是一回事。

王夫之与顾炎武
王夫之、顾炎武这么说,还比较和缓。黄宗羲说得更直接。他说三代以下的君主都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个个都坏透了。后来的唐甄借着这个思路继续发挥,干脆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这么说看似离经叛道,其实并非忽然冒出来的奇异思想。它是符合先秦儒家的本意的。就算张载、朱熹他们看了这些话,多半会觉得狷介偏激,但不会认为是邪说。
我觉得,很多读书人内心深处恐怕都曾冒出类似的念头,只是有的不敢说,有的不敢往深里想。但不管怎么说,儒家本质上是伦理本位的、民生本位的。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和儒家的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是冲突矛盾的。
02
但是,不管这些读书人怎么发牢骚,他们也不主张废黜君主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先是劈头盖脸把君主们骂了一顿,后来就提出很多改良方案,但改来改去,也没有把君主这个角色去掉。
为什么呢?是因为黄宗羲就是喜欢在上头有个皇帝吗?
当然不是。他这么说,只有一个原因:他无从想象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
其实不光是黄宗羲,古代儒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未必真喜欢君主,但是他们重视秩序。一个社会必须有秩序,否则就变成了暴力丛林。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秩序怎么可能维持呢?他们想象不出来。
不光儒生想象不出来,道家、法家、墨家都想象不出来。墨翟再怎么注重非攻兼爱,也要在上头竖个“天子”;老子再主张小国寡民,要有在上头安个“圣人”。这也不能怪他们,人确实很难想象出一个自己从没见过的东西。就像你想象不出一种从没见过的颜色,科幻电影导演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地球影子的星球,古代读书人也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
他们不是笨,更不是贱骨头,就是单纯的缺乏思想资源。
就拿黄宗羲来说,如果测智商的话,他肯定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普通人。但是现代人读《明夷待访录》的时候,佩服之余,肯定还是会摇头。它提供的那些改良方案简直可以说是幼稚。这当然是我们的后见之明。并不是我们比他们高明,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已经超过了那个时代。
我们可以拿《明夷待访录》和《论法的精神》作比较,老实说,真是高下立判,后面明显比前者要靠谱。但是,这绝不是因为孟德斯鸠一定比黄宗羲聪明。说到底,无非是孟德斯鸠知道的东西,黄宗羲没有机会知道。
这方面,西方学者确实占了便宜。西方文明是从希腊、罗马演变过来的。希腊、罗马和中国相比有个极大的区别。中国比较早熟,定型得也比较早,而希腊罗马的政体五花八门,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民主制、共和制、寡头制、帝制等等,它们都尝试过。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一定是好事,因为这种转换往往伴随着动荡。但是人类的政治经验往往是从实践摸索中总结而来。
有这些历史实践,不要说孟德斯鸠,即便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也比王夫之、黄宗羲他们更有政治洞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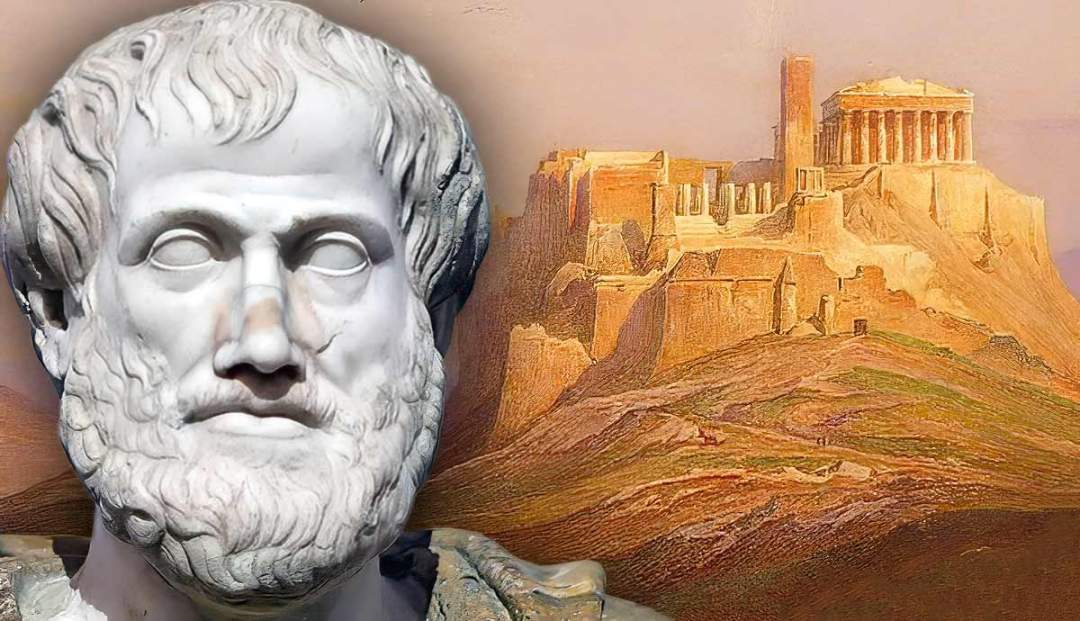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比较过各种政体的优劣
无他,不过是因为他亲眼见过而已
黄宗羲纵然聪明绝顶,也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帝王而有秩序的社会。就算你告诉他,他也不会相信那套玩意真能运转。但是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孟德斯鸠就能想象出来,因为帝制也好、共和也好,他们都亲眼见过。他们知道那套东西能运转,运转好坏不说,但肯定能运转。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怪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想象力都要有个现实的抓手,没有抓手,你让他们平白无故地想,当然是想不出来的。换上谁都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中国读书人第一次知道外国的总统啊议会啊,就受到极大的震撼。如果黄宗羲能听说那些东西,他肯定能写出升级版的《明夷待访录》,把君主这个位子给拿掉。
说句题外话,有时候我们哪怕不知道一个东西的原理,但光知道它的存在,就可能引起一次大震撼,大变革。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能够远远地观测到外星文明,看到某种奇怪的技术能够在那里存在,哪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背后的道理,光是这种“知道”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地球文明。
还是说回到历史。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但实际上中国文化人了解外国的情形,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然后不到50年,帝制就被推翻了。放到历史上看,这个速度算是很快了。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也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骨子里就非要忠君。它没那么贱。说到底,它以前只是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选择而已。
0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三代之治”。
黄宗羲也好,唐甄也好,痛骂帝王的时候,都加了个前提,就是在“三代之下”,帝王们才那么坏。至于尧舜禹汤的时代,君主们都好的不得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回到”三代”的美好状态。
在现代人看来,这就是复古的妄想,正是儒家迂腐荒谬之处。
但是——那些读书人真相信有个极其美好的“三代之治”吗?
普通人也许信,但是对于精英知识分子,就不太好说。可能有点信,但也未必全信。这就像他们对待因果报应的说法。纪晓岚他们就说:“因果报应是没有的,只不过以神道设教,诱哄愚民行善罢了,事情虽然不是真的,但动机还是好的。”
我觉得,他们对于“三代之治”多少就点这个意思。

想象中的三代之治
那些文化人都熟读历史。他们难道不知道夏商周也充满了动荡吗?《史记》已经把那段历史美化过了,但就算是翻翻《史记》也能知道,那几个朝代并不太平。夏朝刚建国就差点亡了。商朝在纣王之前,也动不动就“道衰”,“淫乱”。周朝一会儿是大王淹死,一会儿是国人暴动,绝对谈不上完美。
就算尧舜禹汤这几个人物,古代的《竹书纪年》里也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古代人对此也是知道的。李白写诗的时候就说:“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当然,其他文化精英们没有李白那么大嘴巴,一般是避而不谈。但不谈不等于心里没这么想过。曹丕当上皇帝的时候,就说过:“我现在才知道尧舜禅让是怎么回事了!”他能明白的事,难道别人就傻乎乎地都没想过吗?
还是那句话,古人只是知识资源匮乏些,智力并没有问题。我们能明白的道理,他们也能明白。比方说,大家可以看看苏洵的文章,他就皮里阳秋,找机会刺几句尧舜禹汤,还说什么《易经》里的道理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圣人故意写的晦涩,好让大家佩服,死心塌地的信仰经书,要是拧干了说成大白话,你们就不尊重了。古人腹黑的程度,有时候我们都难以想象。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称赞“三代之治”呢?
当然,也许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正我觉得,他们多少有点“借钟馗打鬼”的意思。那些精英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也不敢提出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方案,但是对君主又不满意,就用“三代之治”的神话来压君主:
“别以为自己挺不错了!跟真正好的比,你还差得远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抽掉了“三代之治”的神话,他们又该怎么去压皇帝呢?唐甄说“天下帝王都是贼”,黄宗羲说“天下君主都是自私鬼”,既然这样,当今天子凭什么就不能躺平呢?
所以,一定要有不是贼的君主“尧舜禹汤”,哪怕历史上没有,编也要编出来。
我不敢说那些儒家的读书人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了个“尧舜禹汤”,确实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然的话,连进谏的奏折都不好写。至于法家为什么不信这个神话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因为实在没这个必要。
话说远一点。在民国时代,鲁迅他们又何尝不是“借钟馗打鬼”?鲁迅那一代往往对传统文化大加抨击,却很少攻击西洋文化的黑暗面。现在看来,他们有些话颇为过头,甚至有双标之嫌。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人盈野,规模之大,骇人听闻。但是鲁迅他们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批评西洋人的好战野蛮。有人提到一战中的暴行,鲁迅还在《热风》随感里偏要说,“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算得什么希奇?”又说:“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用现在的网络用语来说,这就是“反思怪”。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借钟馗打鬼”?就像古代读书人拿“三代之治”做钟馗一样,鲁迅他们也无非是拿西洋做钟馗,以衬托当下的不好之处,催着它去改。至于西洋真是不是那样好,那里的老百姓是幸福无比还是一塌糊涂,鲁迅他们并不是那么关心。
说白了,也有拿对方当工具用的意思。倘若外面比咱们更坏更糟,那我们就可以躺平了,鲁迅又拿什么做理由去催着大家改变,减少当下的痛苦呢?
如此立论,当然很有可议之处,但是背后的动机确实不能一笔抹杀的。
04
文章不知不觉写长了。结束前再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追究起来,这话未必真是王安石说的,很可能是流言。不过王安石听到流言后,也没有辟谣,也许是不觉得这话有什么错。但是宋朝的知识阶层对这话都很愤怒。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是先进的,反对它的那些读书人是迂腐守旧。
但话说回来,那些反对者真相信“天变足畏”吗?
其实也未必。
汉朝确实流行天人感应之说,但到了宋朝,精英知识分子已经不怎么吃这一套了。所谓“天变”,不过是提供一个让他们放言高论的机会。但是请大家想想,这些读书人无拳无勇,能用来对付皇上的手段又能有什么?还不是用“三代之治”来压他,用天变来吓他,用舆论来约束他。如果把这些都抽掉了,皇上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古代帝王权力本就凌驾在法律之上,如果再告诉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还有什么可以对他稍作约束?当然,某一次皇上的想法可能是对的,天变、祖宗、人言可能是在拖后腿——但如果下次他的想法是错的呢?
当时文化精英对这三句话群起攻之,并不全是出于抽象的理念,也有很现实的考虑。面对皇上,读书人的力量本就弱,这三句话再抽掉了他们仅剩的武器,他们索性都变成法家好了。从这儿看,他们攻击王安石是“申商之学”,其实也不算十足的冤枉。

王安石与司马光
两人的是非对错,真是很难一言概之
我们脱离了历史环境去看古人的言论,往往会有误会。很多时候,他们真的是不得已。他们太弱了,弱者总是困难的。他们总是显得不够理直气壮,总是说得拐弯抹角,总是说得不尽不实,有时显得迂腐,有时又显得偏激。
我们站在历史的彼岸,当然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说:天变是假的,三代之治也是神话。你们倘若连这些都信,那就是愚蠢,倘若自己不信却这么说,就是虚伪!
但是,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他们又有什么好办法吗?
不得已啊,很多时候,无非就是不得已。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